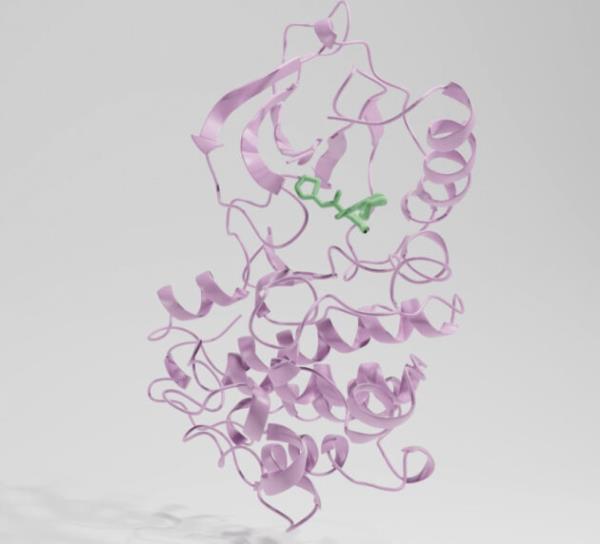传奇喜剧演员兼制片人梅尔·布鲁克斯曾说过一句名言:“悲剧就是当我切到手指时。”“喜剧,”他补充道,“就是你掉进一个露天的阴沟,然后死去。”
如果一扇门砸在你头上呢?我这么问是因为上周末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这是一间露天海滩出租房,通往甲板的纱门从来没有滑得很好,最后因为调整得不完美,完全掉下了栏杆。酒精没有涉及。只有一扇门,几个孩子在用粉笔画画——谢天谢地,他们的位置避开了门快速向下的轨迹——还有我。
门很好,虽然它撞到我的后脑勺上,足以把它的金属框架撞瘪了——我对此感到奇怪的自豪。我也没事,只是有点轻微脑震荡。
但这种震惊是真实的——就像医生要求“认知休息”一样。由于之前没有遇到过这个概念,我发现要实现它非常困难。
我被要求在黑暗的房间里躺72小时,最关键的是,不能看任何屏幕。当我的大脑进行着极其复杂的自我重组时,甚至连书都是禁区。
我懒洋洋地躺在呼呼作响的吊扇下,庆幸自己战胜了死亡(如果不是死神的大门的话),让自己的大脑在几十年没碰过的文件柜里翻找。眼前闪过的不是我的生活。相反,这本书是对最不受重视的章节的慢动作精选,被允许漫无目的地漫游的头脑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回忆起来。
7岁时,我度过了第一个卧床休息的夜晚,有量角器和运动短裤,还有一次到詹兰岩洞的实地考察。我回想起拥有一台科学计算器时的兴奋,以及在期末考试中使用它时的恐惧。
过了一段时间,我需要以有声读物的形式深入研究别人的记忆。过去,磁带书的吸引力一直困扰着我,但作为一个恢复期的人,我把它理解为一种绕过思维挖掘和痴迷倾向的手段。
有一个话题我特别不想去探究:我的孩子们离危险有多近。他们以几厘米之差躲过了悲剧,而这一切的纯粹运气——和荒唐——仍然让我难以理解。
我的认知休息在读了两本有声书和三天后结束了。我已经很多年没睡这么多觉了,现在我对自己的神经突触充满了感激之情。
与此同时,世界又焕然一新了。互联网,一个在我离开它的日子里完全重塑的仙境,夏末的阳光温暖而舒适。由于无法偷看自己的工作收件箱,我对同事们在我不在的时候也能处理得很好感到放心和谦卑。
现在我又一次整天坐在电脑或手机前,我确信认知休息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脑震荡。现在断言屏幕对我们的大脑有什么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我可以说,远离屏幕一段时间对我的大脑大有裨益。
想要阅读《好周末》杂志的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在《悉尼先驱晨报》、《时代》和《布里斯班时报》的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