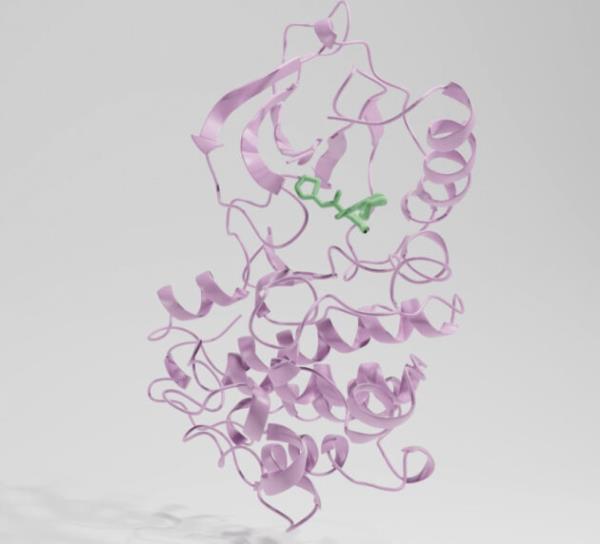来自伦敦的母亲利安德拉(Liandra)本以为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会提前出生,却没想到丈夫会在图书馆停车场把女儿送过来!
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儿子埃利奥在36周零5周的时候出生了。因为他早产了,在我第二次怀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在引导孩子提前出生。所以我从33到34周的时候就有点紧张,因为埃利奥在36周的时候出生了,每个人都说,‘哦,第2个孩子来得早一点!“我已经把一切都收拾好了。而每过一天,我都觉得她已经迟到了。
我的表姐在两次怀孕期间都是我的助产士,所以她一直在照顾我,直到怀孕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每周都有预约。所以在我怀孕39周的时候,她让我打扫卫生。所以我说,‘好吧,我们继续。’
当她做扫描时,她对我说,‘哦,天哪,你的子宫扩张了三到四厘米。你的水在膨胀,宝宝的头在那里。”她一只手在扫,我另一只手抓着她,心想:“哦,天哪,这是不是意味着孩子要出生了?”’她回答说,‘不,因为你不是在主动分娩,你没有宫缩。所以回家吧,放松点,宝宝应该在24到48小时内就会出现。”

所以我让埃利奥和我妈妈在一起过夜,以防万一,这样如果他一夜之间死了我就不用担心照顾他了。我的丈夫达雷尔在工作,要到晚上11点才会回家,所以我很紧张,心想:“天哪,如果这事今晚就发生了怎么办?”但没有,我丈夫回来了,一切都好了。
我昨晚睡了个好觉,早上醒来时,我妈妈把埃利奥扔回给我,我想,‘好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目前还没有这种迹象。所以我就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点我有相当多的能量所以我开始挂一些窗帘在家里,打扫浴室,厨房,做了一些捕捞,洗了一些衣服,开始擦窗户,然后我丈夫在花园里做园艺,和我认为的好,我不妨也试一试,试试吧!”
我和他在花园里耙草埃利奥在睡觉。然后我肚子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就对我丈夫说,‘我想我需要进去坐下来。’但他并没有太在意,他只是说,‘好吧,那好吧。’所以我回到屋里去上厕所,然后埃利奥午睡醒来,他需要换尿布,所以我开始给他换尿布,在他躺在换尿布台上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宫缩。
我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我觉得这正在发生,你需要开始收拾一下,然后进来。’三分钟后,我又经历了第二次宫缩。当我注意到两者之间只有三分钟的间隔时,我想,“哦,天哪,现在真的发生了。”要记住,这只是我第二次宫缩,在清扫和上厕所之间,我没有透露多少信息。
宫缩是如此强烈和令人目眩的疼痛。所以我又打电话给达雷尔,说,‘不,说真的,你得从花园里进来,这事正在发生。’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妈妈,问她是否可以下班回来照顾埃利奥,我又打了第三个电话,是为了分诊,我说,‘我正在宫缩,我要分娩了,我要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助产士问宫缩是多久前开始的。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说这才开始了8分钟,所以我撒了个小谎,说是20分钟。但这还不够,她对我说,‘如果你来这里,而你没有在生产,我就送你回家。’当时我正处于宫缩中期,我只是说‘它正在发生。我进来。”然后她说,‘好吧,如果你确定的话,你以前去过那里一次。所以我只需要告诉你,我可能会送你回家’我说,‘不,不,不,我马上就来。’
它的发生。我来了。
这时,我16个月大的女儿跑来跑去,把我的鞋子从衣柜里扔了出来。我丈夫从种花开始,从头到脚都很脏,但我告诉他没有时间冲澡了。我们下楼去上车,我在楼梯的顶端,我有一个第四收缩,说“我不认为我要让它然后开始有点沮丧,达雷尔说,你知道我们需要至少试着让它。我们只需要上车,我们只要到达那里就会没事的。”
我走到楼梯口,吻别了埃利奥和我妈妈,然后沿着小路回家,第五次宫缩,我意识到他们离得更近了,然后真的开始烦躁起来,说“这不会发生的。”我赶不上了。”但达雷尔只是鼓励我说‘我们上车吧。到医院只需要20分钟。我们会好起来的。我们赶紧去吧。”
我们上了车,右转然后左转。我又宫缩了一次,我的羊水进了车里,宫缩太大了。感觉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疼痛。我好像听到了砰的一声。这是一种万能的喷涌。我表姐前一天告诉我,你的水没了,是因为你扩张了三到四厘米,脑袋还在那儿。当你的羊水消失时,分娩可能会进行得很快。我想没有人预料到它会这么快!
洪水一退去,我就开始喊:“天哪,我想你需要停车,我们需要叫救护车。”婴儿的到来。”我想达雷尔只是想,‘好吧,让我让她保持冷静。’他说‘没关系。我给你表妹打个电话,叫她做接生婆,问问她的意见。”我突然说,‘别叫她,叫救护车吧。’这时,我一边尖叫一边咒骂,基本上就是在说,‘叫辆该死的救护车,把车停下,这个婴儿就来了’,然后他就打了999。
当你的水没有了,分娩可以很快进行。我想没有人预料到它会这么快!
附近有个图书馆,所以我让他把车停在停车场。他把车停在停车场的一个车位上,打开了危险警报器,然后我们就接通了999,我丈夫解释说:“我妻子要生了,她觉得需要推一下。”
我解开安全带,双膝跪地,抓着前座的头枕,因为我们在车的后面有两个汽车座椅,一个是给埃利奥的,另一个是给未出生的孩子的婴儿座椅。我重重地哼了一声,出现了强烈的宫缩,电话里的女士解释说达雷尔需要把两个汽车座椅从车的后面拿出来,这样才能把我弄到后面去,这样我就可以躺下来了。这就像一个喜剧小品——他从前排座位上跳起来,绕着车跑,把一个汽车座椅拿出来,扔到停车场的地板上,然后绕到另一个汽车座椅上,做同样的事情。
999的那位女士开着扩音器问“发生了什么事?”号码是多少?那辆车是什么颜色,你在哪儿,你知道邮政编码吗?”甚至在宫缩的中间,我还在努力听她说话,把车牌号告诉她。
达雷尔把汽车座椅从后座拿出来后,我就把自己塞进了后排的两个前座中间。我翻了个身,两腿张开,我丈夫就在电话里说:‘头来了。它来了!”然后我剧烈的收缩,把脑袋送了出去。与此同时,达雷尔正在打电话给999,她解释说:“头部正在运送,我需要你支撑头部和肩膀。”他只是大喊:“不,头在这里!”她说‘好吧,现在我们来支撑肩膀。’
我认为达雷尔在那一刻陷入了恐慌,就像‘哦,该死,这一切都发生了,没有任何医生和护理人员,没有救护车,婴儿的头还在那里。’我们当时处在11月4度的寒冷天气中,所有的车门都开着,危险都冒着,没人告诉我们没事,也没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达雷尔很恐慌,他开始对我说,‘你需要用力,你需要用力。’但当时我没有宫缩,所以也没什么作用。然后第二次宫缩来了,在他的鼓励下,我给了她一个强大的推力,我想她在第二次宫缩中出来了。

她轻轻地哭了一声,我们都泪如泉涌。但后来她并没有发出更多的声音,于是恐慌又回来了。我们没有毛巾,什么都没有。婴儿袋都还没打开。我觉得它就像被遗弃在地板上的汽车座椅一样。达雷尔刚刚扯下他的套头衫,把它塞在我的屁股下面,以便在她被生产的时候,所以我们把她裹在那件衣服里,把她放在我的肚子上,抚摸她。在记忆中,她有几分钟没有呼吸。但大概只有30秒。就像在那个时候她没有哭一样,她非常忧郁。在那一刻,她还只是个婴儿,我们不知道她的性别。医护人员对我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我们当时的反应是,‘哦,天哪,我们不知道。’我接受了很多。
我们都抱着她,她就哭了。然后达雷尔说,‘我觉得是个女孩!’然后我让她转过身去,说:“是的,是个女孩!”所以我们有了那一刻意识到,‘哦,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她哭了!一切似乎都很好!”但我不认为我们有那种解脱的感觉,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恐慌。
我坐在车后座,把衣服提起来,胸前的婴儿裹在我丈夫的套头衫里,连消毒都没有。达雷尔还在给救护车打电话,救护车解释说我们需要谈谈割断脐带的事。但我们能看到救护车的蓝色灯光。然后这两个可爱的家伙从救护车里探出头来祝贺我们。

他们把罗莎从我身上拖下来,但她和我紧紧地连在一起,所以他们用毯子把她裹起来,紧紧地抱着她,然后我不得不非常靠近地从车里爬出来。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又把我放在救护车的后面。我想我们在那里待了大约20分钟,他们检查了我们的体温和血压,然后开车送我们去巴尼特医院,在路上我还要接生胎盘,这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在医院呆了六个小时才回家。这是疯狂的。我们离开医院,回到家,躺在床上,让她躺在我们旁边的小床上。就像,‘哇,这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