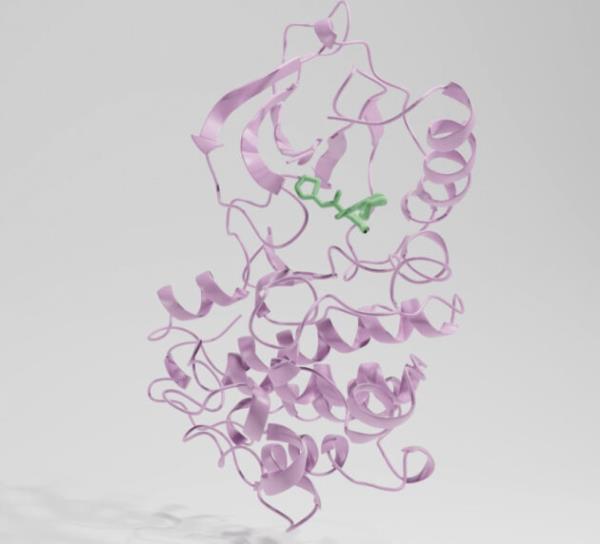我对剖腹产的可能性毫无准备。我真希望在面对他们之前我能知道很多。

当我的医生告诉我需要做剖腹产的那一刻,我开始哭泣。
我通常认为自己很勇敢,但当我被告知我需要做大手术才能生下我的儿子时,我并不勇敢——我被吓坏了。
我本应该有一大堆问题要问的,但我唯一哽咽出来的是“真的吗?”
在做盆腔检查时,我的医生说我没有扩张,在5个小时的宫缩后,她认为我应该扩张。她解释说,我的骨盆很窄,这会让分娩变得困难。然后她邀请我的丈夫来感受我的内心,看看它有多狭窄——这是我既没有预料到,也感到不舒服的事情。
她告诉我,因为我只有36周的怀孕,她不想让难产给我的孩子带来压力。她说,最好是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进行剖腹产,因为这样会减少击中器官的机会。
她说这些都不是在讨论。她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如果我没有那么累的话,也许我现在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问问题。
我已经在医院住了两天了。在一次超声波检查中,他们意识到我的羊水水平很低,所以他们直接把我送到了医院。一到那里,他们就给我接上胎儿监护仪,给我静脉输液、抗生素和类固醇,以加快孩子肺部的发育,然后讨论是否要进行诱导。
不到48小时后,我开始宫缩。在那之后不到6个小时,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在我抽泣的时候,我的儿子被从我身体里切了出来。我要等10分钟才能见到他,再过20分钟左右才能抱着他,给他喂奶。
我非常感激有一个健康的早产儿,不需要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时间。一开始,他是通过剖腹产出生的,这让我感到宽慰,因为我的医生告诉我,他的脐带缠绕在他的脖子上,直到我知道脐带缠绕在脖子上,或称颈带,是非常常见的。
大约37%的足月婴儿出生时都有这种症状。
我最初的解脱变成了别的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当我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时,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情绪:愤怒。
我生气我的妇产科医生,生气我的医院,生气我没有问更多的问题,最生气的是,我被剥夺了“自然”分娩我儿子的机会。
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立即拥抱他的机会,被剥夺了那种瞬间的肌肤接触的机会,被剥夺了我一直想象中的出生的机会。
当然,剖腹产可以挽救生命,但我无法抗拒这种感觉,也许我的剖腹产没有必要。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约32%的分娩是剖腹产,但许多专家认为这个比例太高了。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估计,理想的剖腹产率应该接近10%或15%。
我不是医生,所以很有可能确实需要我的医生——但即使需要,我的医生也向我解释得很好。
结果,那天我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我也觉得自己很自私,因为我没能把生孩子这件事抛在脑后,尤其是当我幸运地活下来并且有了一个健康的男孩的时候。
我并不孤单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剖腹产后会经历一系列的情绪,特别是那些没有计划的、不想要的或不必要的情绪。
当我告诉她我的故事时,国际剖腹产意识网络(ICAN)的副总裁兼董事会成员贾斯汀·亚历山大(Justen Alexander)说:“我自己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
她说:“我认为,没有人能幸免于这种情况,因为你进入这种情况,你看着医疗专业人员,他们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在那一刻,你感到有点无助。”“直到后来你才意识到‘等等,刚才发生了什么?’”
“生存是底部,”亚历山大说。“是的,我们希望人们生存,但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而茁壮成长包括情感健康。”所以,即使你幸存了下来,但如果你受到了情感创伤,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分娩经历,你不应该只是承受它,继续前进。”
她继续说道:“对这件事感到难过是可以的,觉得这是不对的也是可以的。”“去接受心理治疗,向想要帮助你的人寻求建议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告诉那些让你闭嘴的人,‘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是你的错。
我不得不原谅自己没有提前了解更多关于剖腹产的知识,也不知道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剖腹产。
例如,我不知道有些医生会用透明的窗帘让父母尽早见到他们的孩子,也不知道有些医生会让你在手术室里做皮肤接触。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去问他们。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抢劫了。
我还得原谅自己在去医院之前不知道问更多的问题。
我不知道医生的剖宫产率,也不知道医院的政策。知道这些事情可能会影响我剖腹产的机会。
为了原谅自己,我必须找回控制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开始收集信息以防将来我想再要一个孩子。我现在知道,我可以下载一些资源,比如可以问新医生的问题,如果我需要谈话,我可以参加一些支持小组。
对亚历山大来说,能接触到她的医疗记录是有帮助的。这是她回顾医生和护士写的东西的一种方式,她不知道自己会看到它。
“(一开始),这让我更生气,”亚历山大解释说,“但同时,这也激励我为我的下一个孩子做我想做的事。”当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在阅读了记录后,她有信心去找一位新医生,让她尝试剖宫产(VBAC)后顺产,这是亚历山大真正想要的。
至于我,我选择写下我出生的故事。回想起那天的细节——以及我在医院呆的那一周——帮助我建立了自己的时间表,并尽可能地接受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这并没有改变过去,但它帮助我创造了自己的解释——这帮助我释放了一些愤怒。
如果我说我已经完全克服了所有的愤怒,那是在撒谎,但知道我并不孤单会有所帮助。
每天我做更多的研究,我知道我正在收回一些那天被剥夺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