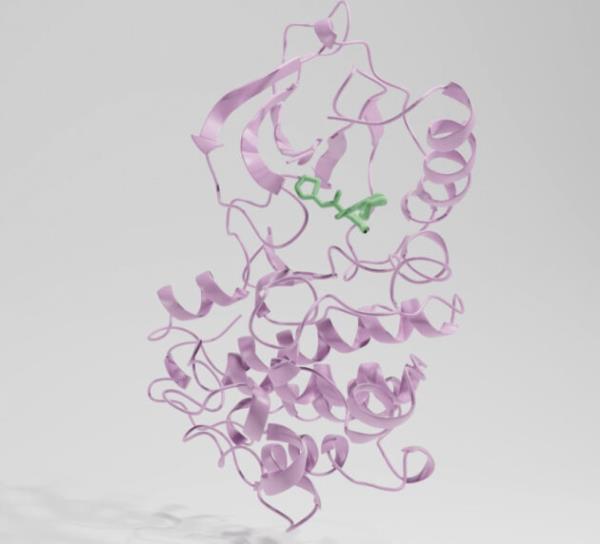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我想我是罗布,”我们的儿子在餐桌上说。
“你说什么?”我问,心想一定是我听错了。他吞下了意大利面。“我想我是罗布,重生了。”
我看着我的丈夫迪恩。他笑了。罗布是我的男朋友。是什么。他27岁去世,我22岁。他17年前去世了,我儿子才9岁,所以算起来不太对头。好像这是他思维的唯一缺陷。
“也许吧!”我把手放在他那甜美圆润的脸颊上。我在那放了一会儿,以防他是对的。他又舀了一勺意大利面,肉酱在他的嘴唇上涂上了一层透明的红色薄膜。
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遇到了我的伴侣罗布。我现在39岁了,这意味着我已经爱了他将近一半的时间。尽管他在2005年突然意外地去世了。也就是说,我哀悼他去世的那些年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年。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我有趣、善良或勇敢。虽然他曾经告诉过我这些事。
罗伯突然去世后,我被告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时间交朋友。这似乎很荒谬,因为每一毫秒,每一秒,每一分钟,我都在离上次握他的手更远。睡在他身边。然而。悲伤既使时间膨胀又使时间压缩。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仿佛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他的书中,在雨中在池塘里游泳,乔治•桑德斯说,这一时期的作家问道:“我们该如何生活在快乐的世界似乎要我们爱别人但是大致分离我们从他们最后,无论什么?”我们仍然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在问这个问题。
14年前,我和我的搭档迪恩结婚了。我们有四个有趣的男孩和两只狗,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笑和欢乐,周六的篮球之夜,电影之夜,约会之夜和爱情之夜。如此多的爱。然而我所拥有的爱并不能抵消我的悲伤。它为它腾出了空间。它把它包起来,带着它穿过。我和迪安的生活开始时,我和罗伯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正如反过来也一样。Dean是我最凶猛的保护者,这意味着他凶猛地保护Rob留下的空间。因为他爱我,罗伯是我的一部分。永远都是。
在罗布的忌日,是我的伴侣第一次从我的眼中看到了痛苦。谁说:“我们爱你。”我猜他说这话是在说他自己和孩子们。当他说"我们"时,他说的不是这个人。
我们称之为难以想象的损失,尽管这是谎言。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时,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一些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事情。
罗伯死后九年,我失去了弟弟马修。他只有39岁。有一天他去上班,就再也没回家。他的心。也很突然,出乎意料。即使是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对这件事感到震惊。虽然我已经知道我们爱的人可能会死得太早,但我内心的一部分还是认为我不会再失去他们。就好像我们一生命中注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已经说了我的,非常感谢。然而。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理解悲伤的直接性。震惊。我们可以承认某人的损失和无法言喻的痛苦。我们称之为难以想象的损失,尽管这是谎言。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时,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一些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事情。一个死亡。休克的诊断。一个意外。
我们想象它。我们把损失想象成自己的,它的震撼震撼着我们。“我无法想象……”我们说。尽管我们可以。“我不想想象”才是我们真正的意思。我不想想象这是一种可能。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可以在一瞬间改变。
今年我40岁了。今年,我在这个星球上度过的年数将超过我哥哥。他是我的哥哥。不动。尽管他已经不在了。即使他永远都是。悲伤违背了物理定律。空间和时间。悲伤的形状变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每个阶段重新面对它,重新定位自己。所有这些悲伤的新方式。
在我哥哥去世四周年的那天,我来到幼儿园接我的双胞胎儿子,他们是马修去世八个月后出生的。双胞胎兄弟伊登·马修(Eden Matthew)比他大了一分钟(他经常提醒弟弟这个事实),他的中间名是他一直没能见过的叔叔的名字。
这是新学期的第一周,当我到达学校时,老师告诉我他们今天在讨论中间名。还有一个孩子的名字和姓氏相似,所以他们在讨论如何区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伊甸他的中间名,这使我毛骨悚然。偏偏是今天。马修的名字就像咒语一样。这是一个征兆,我敢肯定。
“所以今天我们叫他伊登·莱昂内尔,”老师告诉我。
“等等,什么?”我说。“莱昂内尔,”她回答说。“他说他的中间名是莱昂内尔。”我笑了起来,刚才还在流泪的眼泪现在变成了笑的眼泪。“他的中间名是马修,”我说。
后来我问伊登这件事,他没有任何解释。他是四个。我刚想到一个名字叫莱昂内尔。我想马特会喜欢的。
悲伤之后的生活什么都不是,一切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黑暗边缘的幽默。世界还在继续运转。当我们爱的人死了,我们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不仅是在身体层面上(因为它的痛苦是如此的极端,这就是它的感觉),而且我们也失去了我们为自己设想的未来。我们本可以过的生活——本可以过的生活——就存在于表面之下,提醒着我们本可以过的生活。
悲伤不是线性的。我们不会快速通过阶段,然后从另一边出来。没有终点。
即使是现在,我还是下意识地拿起电话给我哥哥打电话,然后才想起我做不到。即使现在,我还能看到罗布走在街上。在我意识到那不是他之前,看看他熟悉的肩膀形状。不可能是他。因为也许鬼魂不是死而复生的人,也许鬼魂只是可能性的暗示。总是困扰我们。我们开始思念一种不再属于我们的生活。
关于悲伤和失去的叙述是有某种救赎的弧线的。就好像这次损失是反常的,而不是正常的。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打断了我们的生活,然后人们放下砂锅菜,给我们同情的眼神,然后我们恢复正常的节目。然后,然后,然后。
但悲伤不是线性的。我们不会快速通过阶段,然后从另一边出来。没有终点。我们失去的人还在想念,所以我们想念他们。会继续想念他们。因为我们怎么能不呢?
对于那些被遗忘的人来说,死亡并不是有限的。我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悲伤是残酷的,但它不能用暴力来对付。生活是美好的、可怕的、令人心碎的、不可思议的。它不能被分割开来。它融合在一起,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一个似乎希望我们爱别人,却又将我们与他人分离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快乐地生活?
我想,答案是:我们怎么可能不呢?生活仍在向我们走来。开始是慢慢的,然后一下子就来了。
我的孩子们是听着罗布的名字长大的,他的名字是我丈夫大声说出的。沾着意大利面条的嘴唇在晚餐时谈论轮回,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因为,无论我们如何相信来世,爱情都是可以转世的。我们都以这种方式重生了。
发现,想(Ultimo Press)由娜塔莎沙尔2月2日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