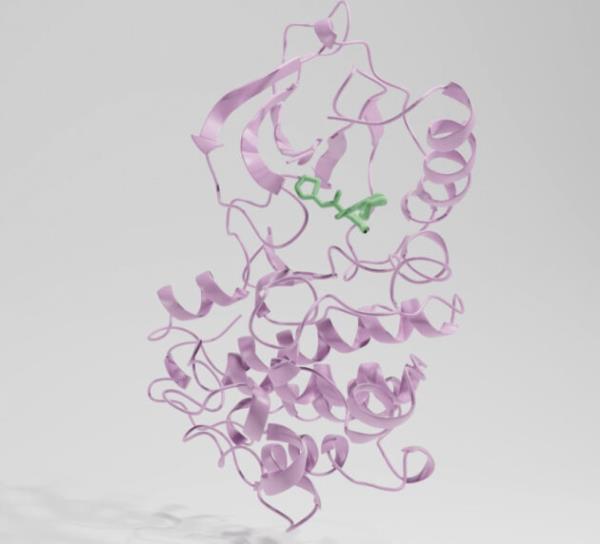如果可以参照好莱坞电影的话,祖母们应该是甜美的、灰白头发的小女士,她们喜欢织毛衣,当刚出炉的巧克力曲奇香味从烤箱中飘出来的时候,她们会把孙子们拉进温暖的怀抱里。
和我一起长大的祖母——我的妈妈——在父母离异后和我的父亲住在隔壁的郊区。她是一个顽强、务实的女人,有一种肮脏的幽默感,喜欢打麻将,喝啤酒后大声打嗝,种西瓜,强迫我们吃东西,穿着在百货商店找到的廉价运动鞋在附近快步走。(她是我认识的最厉害的女人之一,我很荣幸能成为她的孙女。)虽然我爱我的妈妈,但我想知道我的外祖母,我远在加拿大的Por Por,会不会不一样。
我只见过我的可怜一次,那是在我四岁的时候,我记得她爱讲笑话,声音低沉沙哑;剩下的我只能自己想象了。我11岁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她和我要去加拿大旅游,看看波尔波尔。波尔现在已经70多岁了,所以我开始为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而烦恼。
“你会爱上一个陌生人吗?”我在准备旅行的时候问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爱上Por Por了,爱得我都快撑爆了!”
我们一到多伦多,我就变得更加矜持、害羞了,因为我不会说她的语言,她有那么多孙子孙女,我想知道她怎么会有兴趣再多认识一个。除此之外,我感觉不像我自己了。我很情绪化,经常是无缘无故的,而且远离我的兄弟姐妹,我感到非常孤独。当我在严冬被困在异国他乡时,他们却在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一起吃着冰块,一起去海滩。
我只想离开加拿大,所以我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乱发脾气,连续几个小时玩电脑游戏,和妈妈和Por Por保持沉默,不管我睡多少觉,我都莫名其妙地昏昏欲睡。(我不知道,但我这辈子第一次来例假。)
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想要朋友们与非亚裔祖母之间那种亲密关系,但我发现了尴尬和无法沟通(我的Por不会说英语,我说的广东话很蹩脚)。我恨她,默默地吃着她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晚餐。我生气地离开饭桌,然后感到深深的懊悔。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过圣诞节,赠送礼物是我们家表达爱的方式,我们彼此足够亲密,可以制作或购买有意义的礼物,让对方珍惜。”
“我很抱歉对Por Por这么刻薄,”一天晚上,我含泪向妈妈坦白道,我们渐渐入睡。“没关系,”她轻声细语地说。波尔波尔有七个孩子。穷穷理解。”
我们决定延长我们的旅行,在加拿大过圣诞节,我的堂兄、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将主持这次活动。整整一天,当我表哥的孩子们撕开他们的礼物时,我都快哭出来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过圣诞节,赠送礼物是我们家表达爱的方式,我们彼此足够亲密,可以制作或购买有意义的礼物,让对方珍惜。
我收到的唯一一份礼物是我表妹妻子的一个亲戚送的,打开时我有点迷惑不解:那是一枚猫头鹰形状的花哨胸针,红宝石般的眼睛在盒子里威胁地瞪着我。我被这一举动感动了,但也被打动了——这枚胸针显然是一个转送的,因为它更适合一个领养老金的人,而不是一个11岁的孩子。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一个人在家里闷闷不乐地转来转去,就像一个即将成为青少年的孩子一样喜怒无常。下午晚些时候,我的Por挥手让我到她安静地坐在客厅角落里的地方。“文仪,这是给你的。”她递给我一个红包,里面装着钱,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
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尽管她有无数的孙辈和曾孙辈,尽管我们彼此知之甚少,但我对她还是很重要的。她爱我,而且用一种她觉得舒服的方式来表达她的爱。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和感动的姿态,比我为自己创造的任何虚假的期望都要好。
现在,差不多20年过去了,我的Por Por已经去世了。但我还有她送给我的钱。
编辑过的摘自米歇尔·洛(Michelle Law)所著的《亚洲女孩正在前进》(Asian Girls Are Going Places, Hardie Grant),现正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