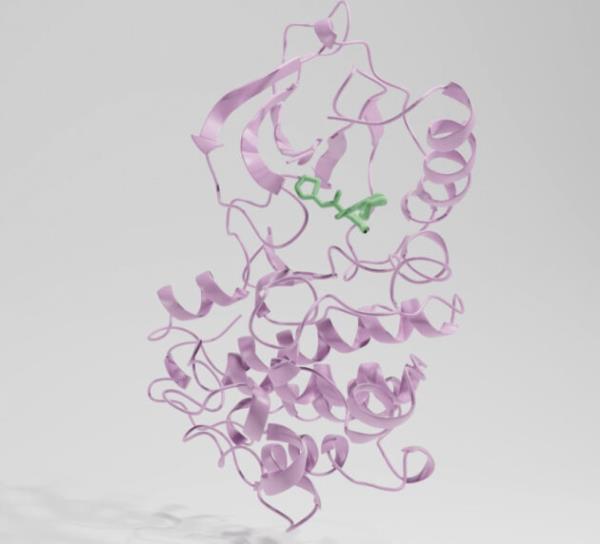我刚开始和新认识的人约会,就因为害怕一种未知的病毒,我们分开了四个星期。书信写作一开始是一种流行的东西,但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每周两次的、在意大利信纸上用草书书写的东西。我会在纸上洒上香水,然后用淡紫色蜡封好,中间凸出我姓名的首字母的厚厚的信封封好。我用的是华丽的钢笔,尽管我对键盘的熟练程度意味着我已经几十年没有手写过任何东西了。写信成了一种小小的痴迷;我差点就买一支羽毛笔了。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兴奋。
一想到要写信,我就兴奋不已,就像我实际上经常写信一样;它们象征着一个53岁的人仍然可以恋爱。我17岁的儿子发现一个粉红色的信封躺在我的车后座上,它的气味扑鼻而来,盖过了车里其他的气味——一把湿伞,一些打开一半的薄荷糖——我17岁的儿子称我们为“尴尬的夫妇”。我把这当成一种恭维,尽管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是恭维。
我和我的情人都50多岁了,我们在30多年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邂逅之后又相遇了:一次高中四人约会。但今天我们都戴着眼镜,而且我的听力也变得有些不太好,所以如果他恭维我,而我正躺着,把坏耳朵压在胳膊上,我不得不说:“你说什么?”我仍然记得年轻时的感觉。
我的高中生活被一段糟糕的关系所玷污,那个男孩总是说我看起来不怎么样。所以,这么多年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男人,他不仅做了我当时希望我的青少年情人做的所有事情,而且还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时光——只是现在,以一种好的方式。毕竟,在他的浪漫史上,我是唯一一个看过他的学校话剧《我女儿婚礼上的龙虾》(Lobster at My Daughter 's Wedding)的女人,坦率地说,我对这个人在完全成熟之前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新爱情的兴奋,都是令人陶醉的。
在我给他寄信的时候,我的伴侣给我寄来了一些歌曲让我听——一盘现代合辑——偶尔还会把咖啡放在我的门口。我的每封信语气都很相似,在没有新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充满了想说新事情的渴望。我在上面写满了我那天做过的事情的片段(在街区散步时轻拍邻居的猫,有时会占据一整段时间)和几行诗。
手写的便条有一些永恒而坚实的东西,是用墨水在纸上记录下的对现在的庆祝,比短信或电子邮件更能给明天带来安慰。
偶尔我会附上一份报纸的剪报,我还是买了IRL。我儿子讨厌我用他那个时代的首字母缩写,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培养了我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我的首字母和我的伴侣的首字母的一面,一颗围绕着这对恋人的心。
文字总是在安慰我。在一次禁闭大扫除中,我发现了妈妈写给我的所有生日贺卡。其中一封是这样开头的:“致我亲爱的女儿雷切尔,我常想,你是否意识到你对我是多么的珍贵……”她死后,给我留下了一些她的其他宝贝,包括一个又粗又粗的金链手链。虽然这些信还放在保险箱里,但我总是和她在一起,放在我书房书架高处的一个盒子里。当我需要食物或提醒我她的存在时,我就会抽出这些书来读,一遍又一遍。
当我们为期四周的自我隔离结束时,我并不为再次见到我的伴侣而感到遗憾——但我为我不能再给他写信而感到遗憾。手写的便条有一种永恒而坚实的意义,是用墨水在纸上记录下的对当下的赞美,也许比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帖子更能给人带来慰藉。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和现实生活中的伴侣谈笑,我会把我的写信技巧收起来,当我再次需要它们的时候,我会像我母亲的信一样,小心地、有目的地拿出来。
欲了解更多《美好周末》杂志的内容,请访问我们在《悉尼先驱晨报》、《时代》和《布里斯班时报》的页面。
每个星期六早上,最好的“好周末”都会送到你的收件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