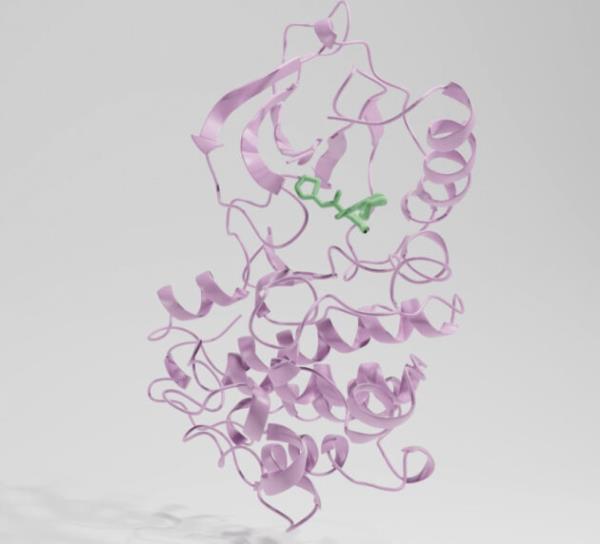2017年7月,皮特和史蒂夫·梅去看望他们的兄弟马克,马克住在新南威尔士州阿米代尔东部的奥克斯利野生河流国家公园。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皮特的两个成年孩子。他们一起艰难跋涉进入峡谷,经过一天的搜寻,他们找到了一个用油布和绳子搭成的庇护所。入口处是马克的尸体。然后,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在电话范围之外,他们突然感到悲伤,埋葬了他。
2019年4月,皮特同意带我去马克住过的地方。我早早地到达了阿米代尔,在一家咖啡馆里撑着雨伞避风等候。皮特出现了,他的脸大而友好。我们聊着家人,吃着厚厚的冷白吐司。
皮特开车送我们去了希尔格罗夫。在路上,他简述了马克的生活。在学校很出色,在家里却很困难。获得奖学金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法律,吸食海洛因,然后在丛林里生活了35年。
在我们穿过牛圈的时候,我们的谈话被我进进出出的车门打断了。最后,我们经过了一个小山丘,把车停在了离河岸不远的地方。我们带着行李下了车,沿着一条路堑往前走。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一个简陋的营地。岩石形成了一个壁炉,树后是装着老式工具和帆布帐篷的塑料垃圾箱。
皮特带着我们离开了小路,走下陡峭的河岸,岩石之间长满了稀疏的草丛。他找了几分钟,然后坚定地向悬崖走去。我跟了上去,发现他发现了一串台阶。它们是由不匹配的木材、几根管子和铁丝网制成的。有了这些台阶,我们走得更快,也更安全,我们很快就滑下了陡坡。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河边。水不流动,而且有臭味。我们在一个长满草的露台上扎营,露台被母橡树遮荫,感觉就像一个户外房间。房间里有一处烹饪区、一座壁炉和用来坐的木柴。垃圾桶里装着烹饪用具和香料。垃圾桶的一个盖子被掀翻了,上面打了几个洞来收集水。虽然已经倒了两年了,但它闻起来还是很香,所以这就是我们喝的水。
帐篷一搭好,皮特就开始做饭。他在火上做着厨师般的手势,谈论着融合烹饪,给我端来蒸粗麦粉和印度菜。它是美味的。
我们洗盘子,喝茶,谈论马克。梅斯一家住在离阿米代尔不远的一个小农场里。他们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他们的天主教信仰是实际的。他们定期去做弥撒,但选择由一位被当地人戏称为“Zip”的牧师主持布道。
有兄弟七人。马克生于1954年,排行第二,比皮特大5岁。他们小时候有时住在一个房间里。马克是私密的:他划定了他那一半的房间,并强制划定了边界。男孩子们玩身体游戏,但他们不喜欢运动。他们去打猎、徒步旅行、骑自行车。他们经常在峡谷里露营,但马克很少和他们在一起。皮特喜欢和他的兄弟们呆在河边。他们捕鱼,有时用聚光灯在浅水中拍摄鳗鱼。一天晚上,由于抓不到任何食物,他们吃了一条黑蛇。
马克是艺术。他创作并上演戏剧。他会给他的兄弟们穿上床单和茶巾,打扮成牧羊人和阿拉伯人。故事情节精心设计,如果兄弟俩做错了什么,他们就会被揍一顿。马克和他父亲之间关系紧张。他们会争吵,马克经常闷闷不乐。
高原之外,天气很暖和。我真想去河边洗掉走路时的汗水。但水是浓稠的,我可以看到在泥里觅食的鳗鱼。相反,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倒进杯子里,递给皮特。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第一年结束后,马克回到了阿米代尔。皮特是13。马克给他讲了学习、聚会、毒品和革命的故事。激动人心的校园生活。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开始吸食海洛因。他的父母担心得心烦意乱。他们经常离开阿米代尔,在堪培拉待很长一段时间,试图帮助他。其他的孩子呆在家里,独自在农场里。在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抢劫了他父母的朋友拥有的一个化学家。他从监狱里出来后,就住在丛林里。
听了皮特的话,我意识到尽管马克离开了他的家人,但他并没有离开他们。他们的母亲总是焦虑不安。检查他是很困难的。早期没有手机,后来也没有信号。马克太偏执狂了,不愿意保留一个邮政信箱。离小镇4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树洞,他有时会在那里传纸条。
皮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5年的圣诞节。像往常一样,马克突然出现了。他骨瘦如柴,手指上沾满了烟草,黝黑的皮肤几乎掩盖不了脸上的骨头。他咳嗽了。
皮特见到他很高兴,但马克却很难融入。他不承认更大的家庭;相反,他谈到了他在灌木丛中的家。马克似乎很希望皮特能来看望他,皮特也希望能有时间去看望他的弟弟。
“我活着的时间那么短,为什么还要为死人操心呢?”既然我现在说不出未说的话,何必去管死人呢?马克离开了这里。返回但不见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
当皮特和我谈话时,一只负鼠从树上下来。它把鼻子伸到我们的锅里,当它找不到任何东西时,它摇了摇尾巴,自信地向我们走来。我递给他一块苏格兰手指饼干,他小心翼翼地用大拇指可对生的爪子接过。
10分钟后,负鼠感到无聊,快步跑进了黑夜。皮特和我跟着它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们走到河对岸,惊动了一群乌龙。那匹公马转过身来,朝我们走来,直到它能辨认出我们不熟悉的气味,然后带着他的母马跑上了长满树木的山坡。
这里的森林不同,更开阔,更干燥,阳光更充足。我们到达了马克的营地。它几乎成了灌木丛的一部分。皮特必须指出搭建帐篷的柱子和搭建壁炉的石头。我觉得自己被打扰了,就像我在写这个故事时多次感觉到的那样。
我把皮特留在那儿半个小时,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一个低矮的岩石堆和一个用未完成的树枝做成的简单十字架。自从警察挖出马克的尸体后,这些材料就被修复了,看起来已经破旧不堪了。
这是对的。另一个纪念碑可能只会被辨认几百年。在丛林里有什么不同?
我们走之前,我问了皮特最后几个问题。像往常一样,他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但他的结论是最终的:“当我对活人的时间如此短暂时,为什么还要为死者操心呢?”既然我现在说不出未说的话,何必去管死人呢?马克离开了这里。返回但不见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他在休息,现在妈妈也可以安心了。”
汤姆·帕特森的《失踪(Allen & Unwin)》现在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