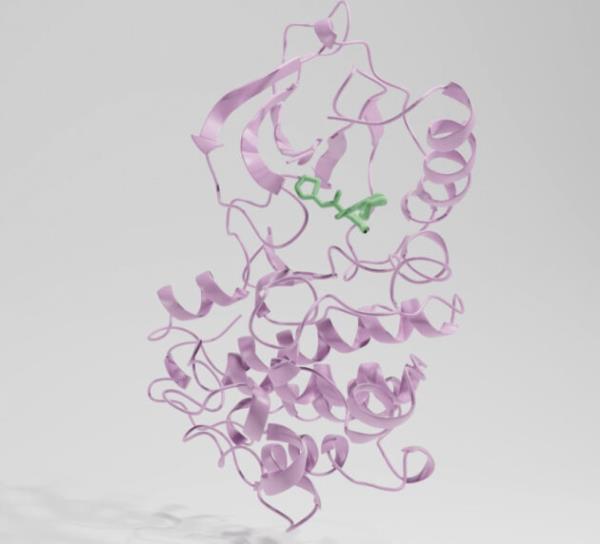在我45岁的时候,我的丈夫比尔决定自愿安乐死,他请求我的支持。当时是2001年,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州,自愿协助死亡都是非法的。自从他13岁的灾难性事故以来,比尔与残疾和偏见斗争了几十年,以获得一个充实和成功的生活。那他为什么选择结束这一切?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不是像比尔这样的人为了过普通的生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2月,我们学院的首席执行官邀请所有的员工在学期结束的下午喝一杯;教工室的两位老师保罗和玛丽打算参加,所以我也跟着去了。大厅里挤满了人,我们站在几百人的嘈杂声中。保罗带着饮料回来,短暂地消失了一会儿,把我们带到旁边的一个小地方。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看上去修长的男人,大概三十出头,坐在轮椅上,旁边有个大块头男人正俯身看着他,可能是为了挡住噪音在说话。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坐轮椅的人。作为一个肩宽肩高的人,他坐得整整齐齐,不时地对另一个人说句话,偶尔喝一杯啤酒。我想记录下每一个细节。他穿着一件浅棕色的夹克和一件奶油色的衬衫,领口有领扣,但没有打领带。我也立刻注意到他只有一条腿,他的左腿。他的脸像一座复杂的雕塑一样匀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微微向后退去,卷曲地披在肩上。他的胡子整洁而略尖,呈浅金棕色。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他似乎竭力避免看向我的方向,尽管我一定在盯着他看;相反,他专注于与他交谈的那个人。我担心他会注意到我盯着他看,并认为这是身体健全的人有时会对残疾人士发出的粗鲁的目光,于是我转过头去看着保罗,但我的周边视野里一直没有出现他。我不时地感到一种轻微的颤抖,表明有人在看我。我希望是他,但不敢去核实。
保罗注意到这两个人已经结束了谈话,他开始向他们走去,歪着头示意我应该跟着他。“嗨,比尔,”他对轮椅上的那个人说,“你好吗?”好久不见了。”他们说了几句话,但由于大厅里拥挤的嘈杂声,我听不太清。保罗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近一些,向比尔靠过去,说:“这是卡洛琳,比尔,我们部门的新成员;卡罗琳,这是比尔。他是我们夜校的负责人。”比尔和我礼貌地互相点头,但他没有微笑,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我觉得这很有趣。我当时35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而且在被介绍给男人时习惯了更热情的问候!后来我发现,他在一段持续了18个月的相当动荡的关系中度过了几年。
保罗和比尔又聊了一会儿,尽管噪音意味着我听不到也无法参与其中。首席执行官开始了他的演讲,每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后来,一些人开始离开。比尔向我们点点头说了声再见,然后坐着轮椅转了个身,飞快地跑开了。他前面的人群左右分开,又跳又笑,想给他让路,好像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我向自己保证,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着更好地了解他。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比尔。我从我家前屋的窗户往外看,看见他正沿着小路走来。他敲了敲门。当我打开它,他比我高;他穿着一套褐色的西装。我正等着他,穿着我最喜欢的裙子和高跟鞋,化着妆。在梦里,他这样来找我,似乎很奇怪。后来梦结束了,但关于它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我。
20年前
6月23日星期一上午10点左右,一辆超速行驶在丹德农山路上的警车发出一声令人作呕的尖叫后刹车,驶入克罗伊登的Woolworths停车场。在汽车的前面有两个警察;韦恩瘫坐在后座上,他告诉他们到这里来,因为他知道他妈妈在上班。
其中一个男人和男孩下了车,急忙进了商店。韦恩把警察领到门口第二个收银机旁,他的母亲面前。这名男子告诉琼,她的儿子被车撞了,目前在Box Hill医院。不!她想,一定是弄错了。韦恩在这里,两个男孩形影不离,所以比尔一定…
但他没有。她期待地看着韦恩,等着他说些什么。他弯腰驼背,脸色苍白,病了,头发蓬乱,上学时穿的套头衫上满是黑色的污渍,但至少她能看到他毫发无损。所以一定是比尔受伤了。“夫人,我们得快点,”警察说。
琼麻木地对她的上司喊道,嘴里嘟囔着什么交通事故,然后抓起自己的夹克,身上还穿着出纳员的外衣,跟着她的大儿子和那个警察回到了车里。当他们开车离开停车场时,她意识到自己没想过给丈夫阿德里安(Adrian)打电话,他在消防队上完夜班后还在家里睡觉。
汽车一回到主干道上,琼就注意到他们在闯红灯,警报器在鸣叫,其他车辆要么减速,要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她还是很困惑,于是转向韦恩。“发生了什么事?他伤得重吗?”韦恩默默地点了点头,结结巴巴地说:“他的自行车,它……”他说不出别的了。他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看到的发生在他哥哥身上的事。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警察转过身说:“我们想在他……”当他看到她的脸时,他简直无法把话说完。
即使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比尔的病历也不容易读懂。在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比尔告诉我他的事故及其后果的故事。他简要地叙述了他漫长的住院生活。在我看来,他的叙述是如此遥远,如此不带感情地讲述,而且常常是简短的,以至于我总是难以想象他处于昏迷状态的样子,多年来无法正常说话或呼吸,他的脊柱和神经疾病在头六个月里没有被诊断出来。我只是无法将这一切与一个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人联系起来,在我们在一起的最初几年里,他看起来健康状况很好,在我们相遇之前的十多年里,他已经克服了大部分生理障碍。现在,我第一次详细回顾了比尔的病史,他在生理和心理上所做的几乎超乎常人的努力令我震惊。
比尔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来控制他最紧迫的健康问题,在这种许多人可能会放弃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为自己重建一个积极、有意义的生活。他不得不重新学习几乎所有的东西——咳嗽和正常呼吸,说话,使用轮椅,管理身体机能大大下降的身体。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用左手来做,包括写作,因为他的右手再也不能进行良好的运动控制,他的右臂也没有多少力量。
比尔在心理上所作的巨大努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首先,接受毁灭性的伤害,然后是多年的医院治疗;然后是构建一个新的“自我”的需要,我们都试图使之或多或少“正常”和连贯的心理过程的复杂互动,这是我们在与他人和世界的所有互动中都需要的。我们知道,在童年和青春期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助于塑造一个人的心理,无论是好是坏。一个13岁的男孩遭受了如此毁灭性的创伤,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与人交流,多年来学校教育中断,想到这些对他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简直是太痛苦了;最糟糕的可能是,至少在住院的前六个月,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医疗“问题”。这样的想法让我们看到,比尔在失去了大部分青少年时光后,从年轻生活的废墟中重建一个“正常”的自我必须付出什么代价。
卡罗琳·李的《选择生存,选择死亡:我丈夫的回忆录》(澳大利亚学术出版社)现在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