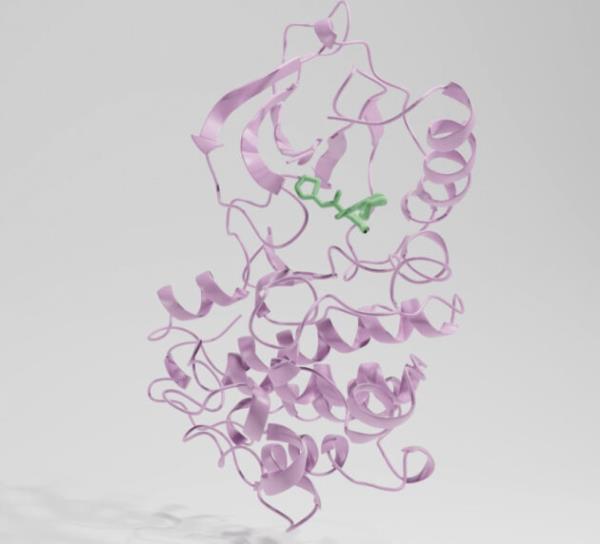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捕梦网和星女郎。三个姐妹。每隔一年。一个豆荚里有三颗豌豆。大家都这么说。它已经这样快50年了。
我是老大,是狼群的首领,专横又外向。捕梦网是中间的一个,非常忠诚,安抚,善良和温和。女明星是最年轻的,是黑暗的异类,是杰出的不墨守成规的人。我们是如此的亲密,连我们的父母都不能打破我们的联系。他们在舞台上盘旋,时不时地冲进来重新布置布景,或者在路上上演,但大部分的表演他们都坐在观众席上。
在我们跨越全球的童年时代,经常发生的剧变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了。另一所学校,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并不重要。我们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直到现在。
在一个寒冷的秋夜,“星女孩”走进她郊外的后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纸条。没有解释。她是一名母亲和妻子,是一名获得沃克利奖(Walkley)的记者,拥有硕士学位,是各州总理的媒体顾问。是什么迫使她结束了一个我想其他人也会献出生命的生命?
只打了一个电话,我的世界就一片黑暗。这就像被一股原子波炸飞一样——这种冲击以暴力的慢动作把我甩出了身体。我被抛向空中就像一个挣扎的碰撞测试假人没有安全气囊来救我。我砰的一声降落了,在一个寒冷的核冬天被活埋了,放射性沉降物像致命的雪花一样落在我周围。
钙质正在从我的骨头中渗出。原来我胸腔的地方有个黑色的裂口。我可以把我的手穿过自己。令人窒息的沉默本来是可以忍受的,但现在不是这样。我的脑袋里有一种喉音在嚎叫。折磨哭。痛苦的哭泣。窒息呜咽。我听不出那声音,但我知道它是我的。我不知道失去亲人会引发这样的声音攻击,发自内心。这是一首只有我能听到的、持续不断的、不和谐的奏鸣曲。第二天早上,我拉开窗帘,面对没有她的第一天。
只打了一个电话,我的世界就一片黑暗。这就像被一股原子波炸飞一样——这种冲击以暴力的慢动作把我甩出了身体。
耀眼的阳光使我目眩。这是白炽灯。几乎不雅。这是悲伤对你开的残忍的玩笑。对于世界上其他的人来说,这一天充满了快乐。悉尼的微风带着女学生兴奋的喋喋不休;一群叽叽喳喳的鹦鹉在附近的屋顶上密谋。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我丈夫马克正在给金盏花浇水。它们上下摆动,鞠躬,用它们明黄色的脸换取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之吻。
但我的镜片上有一层厚厚的凡士林。而且不是多丽丝日演的那种。世界是模糊和模糊的,没有调整表盘可以使它回到焦点。就像在老国王十字车站醉醺醺的早晨。还记得这些吗?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夜晚,穿着可笑的高跟鞋从阿尔伯里酒吧(the Albury)走到男爵酒吧(Barons),与保镖、妓女、骗子和足球运动员共享酒吧凳子。之后,会有记忆的碎片一辆出租车回家,吸在清凉的空气从开着的窗口保持有时头晕,摸索钥匙,传递出在沙发上的深夜音乐愤怒,只有用药棉头后,在一个非常可爱的迷乱,电视上模糊的白噪声。我们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节目。
现在,“正常”这个词让人感觉很不合适,很可怜。我不想要正常。我想要一股超自然力量让她起死回生。
我被逃离的冲动所淹没——打开公寓的门,跑啊跑,不去任何特定的地方,只是离开我自己。感受微风用热泪刺痛我的眼睛,让我的肺重新充满生机。要是惯性没那么严重就好了。我的腿动不了。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你已经做过无数次了。但这是绝望。我是一个被弄皱了的木偶,等着木偶师来让我复活。独自在宇宙中。
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一种混乱的气氛捉弄了我,我忘记了昨晚的电话。我脑海中愉快地开始检查清单我计划有:扫描我的邮件,把水壶,切一些水果当早餐,付煤气费,减少干洗,买些羊肉晚餐……然后生命不可承受之黑暗冲回来,冲我的直觉。
我弯下腰,一瘸一拐地走进浴室,往脸上泼水,小心翼翼地不去照镜子。我还没准备好见到自己。
我扣上我的都市盔甲——打底裤、t恤、羽绒服、跑步服、帽子和太阳镜——希望溜到街上时,不会看到任何昨天认识我的人。
那是以前的我。当我摇摇晃晃地沿着麦克利街走着的时候,港口刮起一阵狂风,吹得那些梧桐树瑟瑟发抖。我拉上夹克的拉链,把手伸进口袋。我拐进了查里斯大道上的咖啡馆。一群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当地人焦急地排队穿过人行道。他们的早茶去纤颤的速度总是不够快。我在排队的时候发现了几个邻居,不过谢天谢地,他们都在忙着玩手机,没有注意到那个鬼魂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如果有人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就崩溃。
我朝麦克尔霍恩楼梯走去,它穿过山脊,一直延伸到伍鲁穆卢湾。当地人称之为“末日阶梯”,这是有道理的。这三段共113级的飞行将使除了最健康的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变成一个吸着气的真空袋。几个世纪以来,饱受煎熬的水手和海湾的工人阶级,在十字架的召唤下,走上了这些台阶。
当我跌跌撞撞地摔下来,稳住金属栏杆时,我经过那些正在进行晨跑的人。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所追随的欲望的脚步。或者那就是他们想要清除的恶魔。也许“通往罪恶的阶梯”更合适。
我穿过考伯码头路(Cowpers Wharf Road),来到花园岛(Garden Island)海军基地的围栏线。在那里,一群炮灰色的战舰停泊在哈利车轮咖啡馆(Harry’s Cafe de Wheels)的馅饼车旁。路边散落着陈腐的面包卷,一群凤头鹦鹉和恭敬的鸽子咯咯地贪婪地啄食着这意想不到的自助餐。
我慢跑上楼,穿过金合欢树丛,来到麦加利夫人道,然后沿着土路爬上斜坡。随着树木越挤越近,城市的喧嚣开始变得低沉起来。两只无花果鸟在头顶上咕咕叫。船的反浪荡漾着,拂过灌木丛生的岩石。还有另一种声音……我还在提高自己的感官。是的,我现在能听到它了,它的声音比我心跳的声音还高,它是沙沙作响的树叶中几乎听不到的低语,希望我能走得更深一些。我曾多次在花园散步时听到过这些低语,但这是我第一次深入倾听,让振动穿过我,并与我的内心融合。我闭上眼睛,这嗡嗡的声音形成了像地球一样古老的温柔节奏。
母橡树和桉树靠得更近了。我的皮肤因一个看不见的拥抱而刺痛。我们之间没有话可说,这些树似乎直觉地知道我需要什么:开放和封闭。
和这棵树在一起,在这大自然的楔子里,我感觉我可以独自坐着而不感到孤立。
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在安德鲁查尔顿游泳池的上方,我坐在草地上,潮湿的泥土的气味从树根中散发出来。我身体的麻木感开始融化,就像缓慢移动的冰川穿过岩石峡湾一样。
在这寂静中,有空间倾听我汹涌的思绪。我的头脑一片混乱,船在一个狂野的,噩梦般的海岸线上失事了,危险地倾斜着,离水线只有几英寸。当我向平静屈服时,汹涌的情感汇集成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未成形的话:你是她的姐姐。保护她的安全是你的职责。你怎么能这么彻底地辜负她?
我抬头一看,发现头顶上所有的树枝都属于一棵孤零零的树——一棵高耸的莫尔顿湾无花果树,四周环绕着一条木制走道。我漫步过去,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树皮,惊叹于深深的山脊和沟槽的粗糙纹理,与我的幽灵般的存在相比,它是多么接地气和持久。
和这棵树在一起,在这大自然的楔子里,我感觉我可以独自坐着而不感到孤立。我可以在这棵树上画画,寻求一种独特的安慰。它就在这里,但别问我什么。这棵树和我周围城市自然的碎片能让我走出悲伤吗?大自然会是我的救世主吗?
生命线:13 11 14
编辑节选自英迪拉·奈都的《星与星之间的空间》(默多克图书),现正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