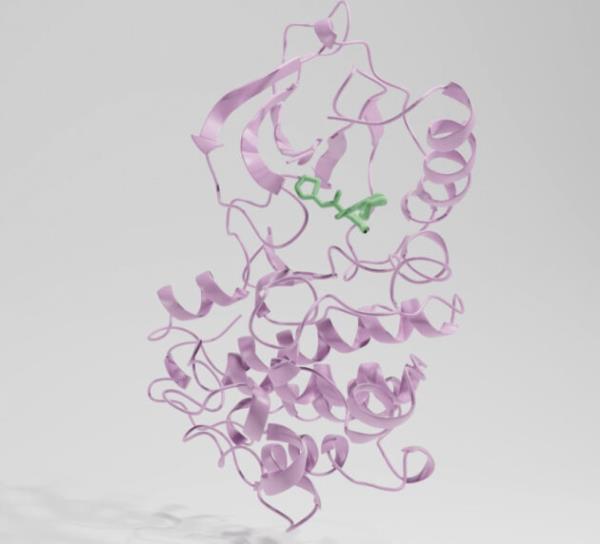菲利克斯和我有我们的午餐散步路线,我们经常看到高中生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坐在墙上,或者在足球场附近闲逛。
有一个女孩,她总是一个人。她大约14岁,深棕色的头发里有一条钴蓝色的条纹。她通常盯着手机或地面,所以蓝色就像向下的箭头。
当我看到她走在我们的街道上时,我的心总是为她而痛。没有一个孩子,不管他们的头发有多酷,想一个人呆着。至少在上课时间不会。如今,她栖息在一块石头上,这是人行道作为景观特色设置的。我认出了那绺蓝色的头发。
我也认出了他的姿势。为了感觉自己更小、更不显眼而故意踩下地板,以及能够在校园里躲避其他人的目光而感到的轻松,尽管只是短暂的。
菲利克斯注意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她的午餐——然后冲过去闻了闻。“如果他吓到你了,对不起。”我说。“他总是对食物感兴趣。”费利克斯摇着尾巴,我给了她一个最灿烂、最友好的微笑。
我想告诉这个女孩,高中将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瞬间,身体、思想和机会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她的一些同学在暑假结束后会变得面如人非。
那些最酷、最吵的孩子将被遗忘,她将在毕业后选择自己的冒险和经历。一位老师或一门学科会在某种程度上触动她的内心,为她提供一条她将永远记住的道路和激情。她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在那里她会感到舒适,而不会对那些她根本不尊重的人的观点感到焦虑。
我当然不知道。我愚蠢的微笑是想告诉这个女孩,我理解她的孤独,她需要暂时逃离学校,从同学们冷漠的目光中找到一个暂时的避风港,这能给她带来安慰。
她没有回以微笑,而是回到手机旁,发出一种“他妈的离我远点”的声音。
当然可以。一个孤独的孩子不需要大人的同情。在青少年时期,只有同龄人的接受才是最重要的。
来自成年人的干扰或愉快的陈词滥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对我们来说,时间过得快得可怕,但在痛苦的青春期,时间拖得慢得要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回忆,那些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真正痛苦的,不管时间有多长。
1980年,我父亲在一个小镇上当老师。我即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上高中,充满信心,我知道我属于这里。这只是我的另一个垫脚石。
后来,父亲在一个项目中获得了一个交换名额,让老师们交换工作和家庭,为期12个月,以体验另一个国家的生活。在我们这里,苏格兰的阿伯丁。我们以前从没坐过飞机!
夏天的圣诞节一过,我们就会马上离开,进入下雪的苏格兰仲冬,我们会住在一栋有250年历史的小别墅里,楼上有阁楼卧室。是的,我们一有机会就会去英国和欧洲旅行。
我们在一条皱皱的床单前摆姿势拍护照照片,床单被扔在晾衣绳上,我们的行李箱里塞满了冬天的羊毛,而我们的泳裤里出汗了。
两周后,当疲惫不堪的法语老师介绍她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时,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邻居家游泳池游泳、头发被太阳晒白的自信女孩被全班同学盯着看。她的外套太大,裙子太长,里面的沙漠靴和白袜子看起来很可笑。这是她第一次感到格格不入。
她的外套太大,裙子太长,里面的沙漠靴和白袜子看起来很可笑。这是她第一次感到格格不入。
没有人表现出一丝兴趣。她已经知道没有人会问她关于澳大利亚的事情。
课间休息时,她慢慢走出数学课,回答“88”时脸红了,听到他们嘲笑她现在才意识到的愚蠢口音。她跟着他们来到衣帽间,假装在等厕所空出来。她不知道这将是她接下来六个月的主要活动。
午餐时间是学校的必修课。拿着票,她会耐心地排队买一盘玉米粉、湿薯片和皱巴巴的豌豆,因为独自站着会让她感到轻松。她会蹑手蹑脚地走到一张空椅子前,喃喃自语道:“CanISitHerePleaseThanks”,然后扑通一声坐下来,躲在刘海后面吃东西。
从来没人说过"不,滚开你这个失败者"他们对她的兴趣和关注是如此之低,以至于用侮辱来承认她需要费一番劲。女孩觉得自己被隐形了。不,更糟,因为她没有自由想走就走,只能待在那里,被人无视。
孩子们会跑出去踢足球、打羽毛球或调情,把她留在后面。在独自坐在衣帽间假装写她的英语日记三个星期后,这个悲伤的女孩发现了图书馆。
这个奇妙的温暖、安静和匿名的地方在午餐时间一直开放。她在每个书架上逛来逛去,如释重负。她喜欢读书,这是一种逃避无聊目光的方式,因为她一个人坐着不会显得尴尬。
Wombles的书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觉得这个电视节目很可爱,知道这些书读起来很简单。它们也太幼稚了,不能被任何人借走,因此可以在下次午餐时间继续使用。
图书管理员知道。她总是在我走进来的时候对我说“你好”,我沉默而苍白,在平常的地方摸着那本书,然后耸着肩膀坐在离入口最远的一张叠层桌子上。
我从来不敢和她说话。我知道她为我感到难过,但看到或听到这种同情会让我难以忍受,我必须永远、永远不要在学校哭。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一个人坐着,似乎被阿伯丁郊区灰色的景色迷住了。在小屋里,我会尽量用最欢快的声音对母亲喊一声“我回来了”,然后把外套挂起来,上楼去。
ABBA的《Super Trouper》专辑会在泪水流下时播放,希望低音的砰砰声能盖过任何啜泣。我凝视着窗外蜿蜒向北的火车轨道,梦想着我又回到了家,与朋友们在一起,有了确定性和安慰,而不是这种可怕的、无情的羞愧、痛苦和隐形感。
周末过得很愉快。我的家人会挤在露营车里,探索村庄、陡峭的城堡、庄园、战场、博物馆和荒野。周日晚上,我们会一起开怀大笑,在上学之前,我会努力让欢乐继续下去,在痛苦、恐惧和厄运再次袭来之前,挤出更多快乐的时光。
一天早上,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前座附近,周围有几个空座位,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拍了拍我的肩膀。
“Hiyeh.”
“呃,嗨。”我回答,声音嘶哑。
“你是澳大利亚人,对吗?”
“是啊。”我喃喃地说,几个月前我就学会了把自己的口音降下来。
“你会游泳吗?”
“是啊,”我回答,抬起头,注意到她可爱的棕色眼睛和头发,凯特·布什会嫉妒的。
“我是帕梅拉,我是金科斯游泳俱乐部的队长,我们八年级需要更多的游泳运动员。你要他来吗?”
她救了我。
帕梅拉救了我。她花时间走到一个孤独、破碎的小灵魂身边,和她说话。
我能为那个蓝头发的女孩做的就是希望她早日找到她的帕梅拉。没有孩子是自己选择独自站着或坐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