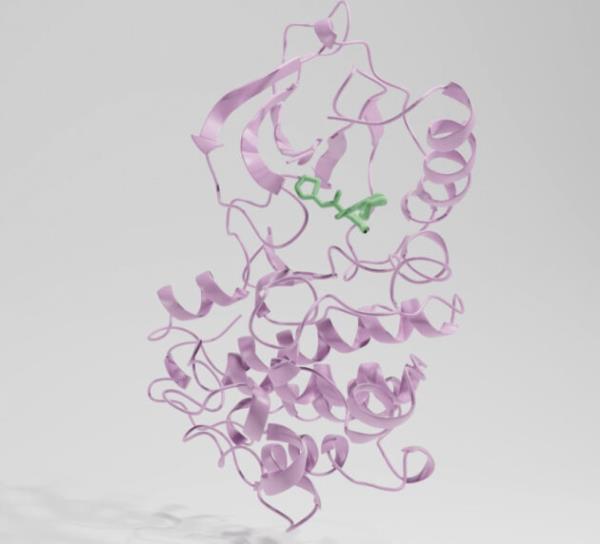作为一个顺性别的白人女性,我有三个孩子,两辆欧洲车,一头染着金色头发,我一生都在冒着被贴上“名头凯伦”标签的风险。
这意味着我尽量不为凯伦(Karen)品牌做任何事,凯伦这个词指的是那些被认为自以为是或要求超出正常范围的女性。例如,我没有把我的租来的邻居们后院的草坪弄进议会。说真的,我只说过两次"我要给时事报打电话"我不太谈论我的百万飞行积分,也不写信给相关人士。
但是。即使我的"我什么都不欠"天线在抽搐,我还是很像凯伦。
场景:周五下午,堪培拉机场。
我是第1000万次被随机选去做爆炸试验的。飞机晚点了,登机口移动了两次。我想都没想就吸进了一包花生糖。我的脸因为注射了肉毒杆菌、皮肤填充剂和激光治疗而变得像核爆一样红。我忘了我可以在圣母酒廊等。
所以,当航班被叫到的时候,我想登机。优先车道形成了,我在前面四排。但是乘务员扫描登机牌时发现我们走错了车道,拒绝让我们通过。我们不得不等待,当其他乘客被放行时,我们宝贵的提前登机资格被耻辱地削弱了。
史上最小的第一世界问题。但后面的女人不能让它休息。“为什么要惩罚我们?””她问道。维珍的员工无视我们,这是凯伦臭名昭著的导火索。
我问他是否知道我们是白金会员,是否关心客户服务,还有,亲爱的达美航空公司,他的经理在哪里,这段独白和我在一次求职面试中说“MOFO”一样让我挥之不去。我很想说我喝醉了或者着魔了,但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clichéd混蛋。
最后,在船上,我仍然很生气,我想我要修理我的新敌人的红色小马车。甚至在飞机起飞前,我就在给客户服务部门的一封愤怒的信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因为他们除了对付一个因为她不是第一个上飞机而大吼大叫的公主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两天后,我丈夫把斯柯达检修了一下。后面的雨刷修好了吗?不,他说。仍在尖叫。“好的,”我说,“我星期一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他们马上就能把它放回去。”我受够了。没有什么比雨刷发出吱吱声更糟糕的了。等。
拐角处新开了一家健身房。第一天上课,老师让我在课间休息。我确信他是有年龄歧视的意思,于是我兴奋起来:“我可不会每周花44美元来休息。提醒我一下你的名字。”
在最后一集里,我确实意识到我是个大输家,但飞机的事让我很担心。
我现在发誓要适当地评估情况,在做出反应之前花点时间,让事情顺其自然。我摄入了大量的镁元素,每天吃一份阿尔迪百香果冰淇淋,减少糖分摄入还找了一位自然疗法专家来倾诉压力。我想知道是什么驱动了这种特权行为。
一个朋友冷笑道:“哈。我今天冲出家门,因为我拿不掉亚马逊包裹上的胶带。我曾让人把一个塑料普拉提戒指用半片雨林和几英里长的胶带包裹着送到世界各地,但我进不去盒子里,我很生气。”
把头发引发的愤怒归咎于严峻时代的流行病、猴痘、口蹄疫、通货膨胀、房价、战争、冬天、科林伍德表演得很好——但事实是,我慢慢地向我中产阶级的生物命运低头,成为名人堂卡伦。
如果有治愈方法或幸存者组织,请告诉我。
Kate Halfpenny是Bad Mother Media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