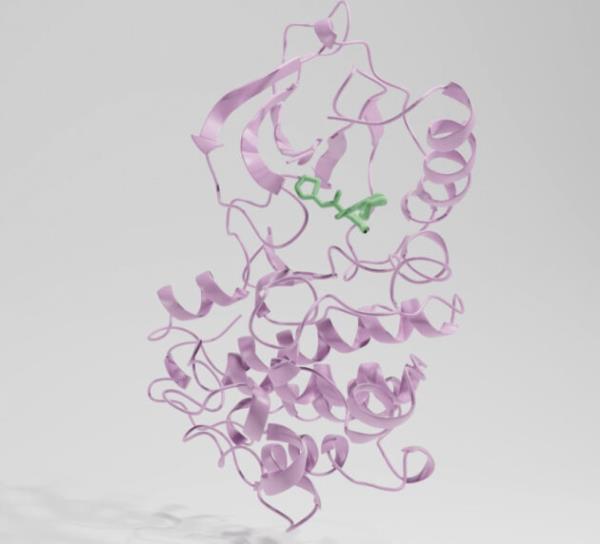这篇报道是8月7日版《星期日生活》的一部分。查看全部11个故事。
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房屋拍卖中,当买家变得咄咄勃勃——要求我们把不属于交易的东西包括进来,并威胁要降低他们商定的报价——我和家人开玩笑说,我会把新鲜的虾缝进我们留下的窗帘的褶边。然后我用漂白剂在后院的草坪上写些粗话,让我们走后的草地慢慢枯萎,露出我们的离别话语。我们对该如何措辞笑了很多次。但我们只是在发泄。我又不会去做那种事。
我不是那种会报复的人。我支持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著名的智慧建议:“当他们往低处走,我们就向高处走。”但正是这种立场,这种对我以牙还牙冲动的拒绝,让我着迷于那些相信用甜品来烹饪的人。
就像我的小说《微不足道》里的主人公丽芙。当她被不公平地从一群朋友中赶出去时,她不会跑开舔她的伤口,而是积极地咬回去。在小说的安全范围内拥抱这种报复的黑暗冲动,我想我将第一次尝到自我管理的正义的滋味。
我没有预料到的是记忆的一闪而过。具体来说,就是对弹力球的记忆:一把橙色的橡胶,比你在学校对面的报亭花几便士就能买到的大理石球要大得多。当球被扔到停机坪上时,会有惊人的反弹。
那时我四岁,刚开始在当地的一所小学上学,在那里有一个非正式的传统,每个大一点的女孩都要领养一个新孩子作为她们的“宝宝”。我希望我能记得选择的过程:是有一排人,还是我们毫无防备地从操场上被带走,就像襁褓中的婴儿被急切的鹳鸟叼走一样?我怀疑是后者。
我的每个同学都在一个漂亮女孩的照料下离开了,她们梳着整齐的长辫子,谈论着芭蕾和马。我被一个“木乃伊”抓住了,她的头发很短,肯定是被剃成那样的——也许是对不断爆发的头虱的反应。她穿着一件又长又奇怪的开衫,不合身。
但正是这种立场,这种对我以牙还牙冲动的拒绝,让我着迷于那些相信用甜品来烹饪的人。
如果她是好心的话,这种令人不安的样子可能毫无意义。但我没有被选为她的“孩子”;我是她的人质。午餐时间是在她那令人窒息的手握中度过的,她坐在一条嵌在散发着酸味的灌木丛中的木凳上,和她的朋友,一个长着一头卷发的男孩,在我耳边低声耳语,把我吓呆了。我只想逃走。
当这个卷发男孩鼓动孩子们在婴儿积木的墙上玩抛接游戏时(当他把做倒立的女孩们赶出去后,也就是拉下她们的裙子,让她们跑开),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他的比赛吸引了一大群竞争对手,所有人都渴望得到他最珍视的东西:那个橙色的弹力球。
这些比赛缺少体育运动,更多的是混战,这意味着有一天,当一个球疯狂地向我飞来时,我可以在混战中不被发现地把它捡起来。“在哪儿去了?卷发男孩问。他的声音很绝望。“在哪儿去了? !”
这个想法瞬间就形成了。我把那把橡皮抓在背后,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假装它的消失是个谜。我的皮肤被危险刺痛,因为我可能只会让我的处境更糟。但是那个男孩和他的朋友偷走了我,偷走了我在学校的快乐,现在我有机会把一些东西偷回来。
一回到家,我就想象着自己一个人在玩那个漂亮的球,但只要把它扔到我们平房的白砖上,妈妈就在那里,坚持要我告诉她球是从哪里来的。我坐在沙发中间的靠垫上,扭动着身体,大腿下面粗粗的绿色粗布;我的父母抱着胳膊站在我旁边。
“是你偷的球吗?”“他们问。我冻结了。我是个好女孩,好女孩是不会说谎的。但我没有词汇来解释为什么这不是盗窃案,而是正义。“不,”我告诉他们。“我找到了。”他们知道我在撒谎。我知道我终究不是一个好女孩。
我在学校的“妈妈”和她的卷发朋友松开了我的手,担心我接下来会偷什么东西,但我没有胜利的感觉。我把球藏在我们那布满蜘蛛网的棚子后面,每次我去取自行车的时候都尽量不去看它,否则我就会被令人作呕的罪恶感所困扰。
正是这种酸涩、挥之不去的余味,可能在潜意识里促使我写了一本关于复仇的书。也许我自己的故事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两个在学校抓我的人被迫羞愧地回顾他们的行为;一个我不再扮演反派角色的版本。
蜘蛛式的小屋早已不复存在,但球本可以存活下来,迁移到我父亲的车库。如果我再看它一眼,我会把它看作是我聪明、勇敢那段时光的纪念。对年轻时的自己的原谅太迟了,但还是要让这里面有一些正义。
朱莉·梅休的《微不足道》(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已经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