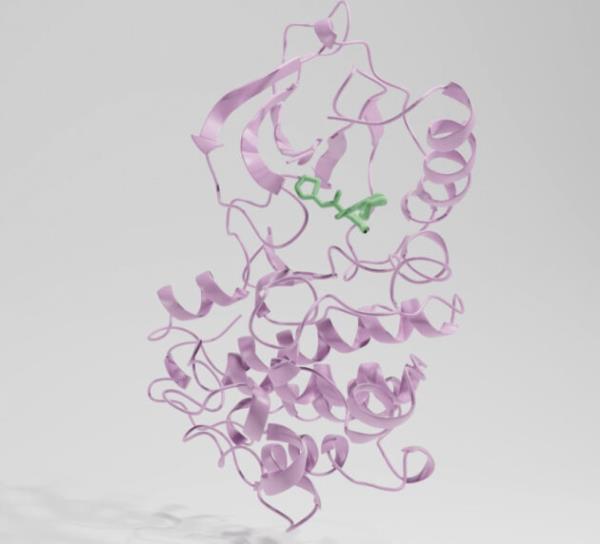迈克尔·伯德是我结识的第一个男孩。那是高中的第一年,我刚从农场回来,我们在课堂上低声交谈,交换笔记。和我一样,他也是红头发,满脸雀斑,很聪明——显然是我的兄弟。其他女孩取笑我,但迈克尔和我都知道我们“只是”朋友。
我一直在想那些“只是”朋友的男人,想知道他们是否和我和女人的友谊有所不同。当然,在异性恋的友谊中,“只是”意味着对永远存在的浪漫和激情的危险的限制——但我想知道这是否真的是一种危险?难道不可能有纯粹的兄弟般的友谊吗?我有五个兄弟,所以他们为我树立了一个不受情爱干扰的人际关系模板——而且,感谢公正的父母,他们有一种平等的意识。
我和兄弟们住在农场里,我骑马上学,玩激烈的游戏,捡鸡蛋,洗碗,赶小牛,到灌木丛里探险,冬天的晚上围坐在炉火旁。我们读书、聊天、争吵,后来,当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火已经变成了煤和灰烬,我们谈论我们是否存在。这一切都可能是某人的梦想吗?能够思考和说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太令人高兴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分享想法时涌动的温暖。
它和住在路对面山里的漫画家菲尔一直是兄弟般的关系。他经常出入我们的房子,表面上是为了借一个洋葱或一杯牛奶,但实际上是为了深入剖析当前的世界状况,或是焦虑地汇报他不安的宝贝女儿。
我们讨论了政治、漫画、创作过程——我最喜欢的菲尔的漫画之一是一位艺术家消失在一幅画中——以及家庭的复杂性和我们共同的天主教背景。他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伴侣和我一样的朋友,所以我不能把他当作唯一的朋友,但我不能把他排除在外,因为他是我唯一一个参加我母亲葬礼的朋友,无论男女。到我的家乡有半天的车程,我没想到会有人来,但当我在教堂里看到菲尔时,我跟着我母亲的灵柩走过通道,我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比我风趣多了,理解能力也强多了。他也更焦虑,更容易感受到世界的重量,这有时会引发我的不耐烦和不宽容。“你不用整天拖着你的十字架到处走,”有一次我们一起度假时,我这样说。他像一只受伤的猫一样跳了起来,然后消失了一整天。当他在晚餐时没有出现时,我向我们小组的其他人承认,这可能是我说的话。我找到他,向他道歉——他原谅了我。
菲尔有很多朋友,他知道如何维系他们,这是男人难得的品质。在他的友谊中,他更加女性化了——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认为这意味着他的友谊没有竞争,他谈论自己的感受就像谈论政治和思想一样多。这个星期,他的女儿正在生第二个孩子,他来拜访了我。我们坐在我悉尼的阳台上,喝着咖啡,像往常一样,剖析这个世界的愚蠢。后来他发了条短信说:“是个女孩。”
和彼得的友谊完全是由另一种材料构成的;一种透明的东西,一种我每次都必须把它想象成现实的联系。起初,他只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同事。我们在他位于一个作家中心的办公室里聊了聊书,书对我们俩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但面对他富有教养的背景,我感到有些不安全感。
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他在成长过程中了解思想、书籍和音乐;我的父母还没有读完小学。我知道的一切都被拼凑起来了。但渐渐地,因为简单的亲近,我们发展出了友谊。
“我有五个兄弟,所以他们为我树立了一个不受情爱干扰的人际关系模板——而且,感谢公正的父母,他们有一种平等的意识。”
从一开始,我们的谈话就让我的大脑充满了一种轻盈的感觉,就好像我的头从肩膀上飘了起来。这并不一定是严肃的——他经常笑,几乎是咯咯地笑,对美味的形象或荒谬的想法。他喜欢原创的、调皮的东西——一种文学上的帕克——我常常觉得我比他更粗糙,他总是比我看得更精细。
一天早上,我听到他在他妻子的墓前唱赞美诗第二十三首。那是山里冬天的一天,在寒冷的蓝天下,敞开的坟墓旁边是冰冻的土地,彼得唱起歌来就像一个受伤的天使,他的声音刚开始只是有些沙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脑子里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听着整首交响乐。他说:“我不知道对那些听不到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在告诉我他的星球上的生活。
后来我到山里去看他。我们在咖啡馆见面,像往常一样畅谈。我和彼得的友谊与其说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不如说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被错误地附在人体内的轻灵温柔的精灵之间的友谊。
与戈登的友谊更为复杂,因为它已经变换了好几次。他一开始是一个朋友的丈夫——一个演员,性格外向,会讲有趣的故事,他会跳进一个房间,在身体上和社交上占据大部分空间。他似乎在表演——而我从来不想成为一个与男性有关的观众。但后来他成为了我的学生,当我教大学入学。尽管很聪明,他还没有完成学业,但他已经30岁了,是一个父亲,准备改变自己的生活。成为他的老师开启了我们都感到自在的文学领域。
有一天,他的妻子因脑溢血而去世,三岁的孩子失去了母亲,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当我们的谈话集中在那个迷路的小男孩身上时,我和戈登的联系加深了。有一种亲密感,一种爱着同一个孩子的连接的温暖,就像父亲和母亲彼此之间没有太多其他的关系。我们仍然在谈论我们的工作和想法——他现在正在学习成为一名律师——我们还在争论,我们都很享受理论分析带来的能量,但真正的联系是作为父母。
几年后,他找到了一个新伙伴,而我也挪了回来,像你一样给朋友的新伙伴腾出空间。我们不像以前那么多话了——事实上,从那以后我想我也没有单独和戈登说过话。现在这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谈论他,但我们之间的联系已经回到了最初的那种轻微的友好。
与男人的友谊的蓝图似乎是由我的兄弟们创造的,他们创造了那些玩耍和工作的夏日,以及围在火堆旁的漫漫寒夜。它让我知道我们都在神秘中——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力量和困惑,这是我与女人和男人的友谊的坚实基础。
帕蒂·米勒的《真正的朋友》(True Friends, UQP)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