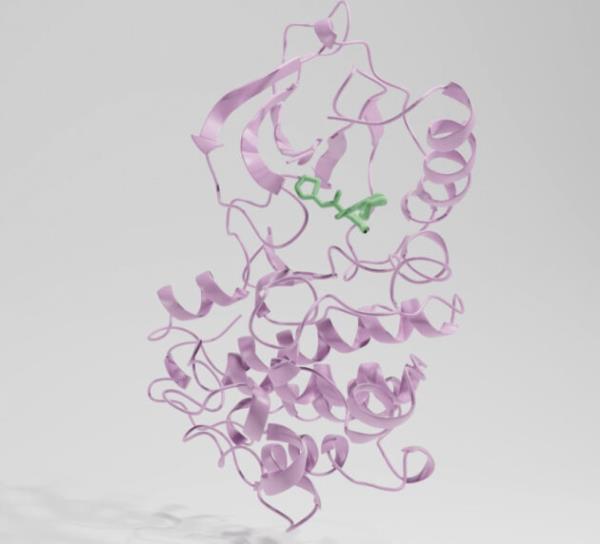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悉尼东郊的水系地带一直在向世界宣传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但似乎与我的西悉尼世界相隔十万八千里。邦迪海滩很难通过公共交通从西郊到达,因此在1996年有人提议修建一条铁路。它被当地的一群邻避者阻止了,他们担心给“西部人”提供通道,认为他们会给该地区带来暴力。与白人的焦虑一样,种族主义被框定为对犯罪的担忧。
这座城市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和过路费,确保了除了最忠实的司机以外,任何人都无法进入昂贵的白人中产阶级海滩。飞涨的房价保护了当地对水路的主导地位,一居室公寓的挂牌价格高达数百万美元。我唯一一次看到海滩是在看《主场与客场》的时候。“真正的”澳大利亚是在电视里阳光普照的海滩上,而不是在我的生活中。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爸爸会带我和妹妹去悉尼西部圣玛丽当地的涟漪游泳池。我会高兴地在浅水区溅起水花,带着敬畏和恐惧看着这些小路。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已经不适合穿孩子的泳衣了,我也不再去游泳池游泳了。
游泳不是我父母从小到就会做的事,也不是他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他们认为泳装是可耻的;男人和女人穿着看起来像内衣的衣服游行。所以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我用至少半袖的衣服遮住胳膊,用宽松的裤子遮住腿。对我来说,多毛的诅咒似乎被放大了,剃刀变钝了,痛苦的脱毛尝试也遭到了挑战,所以我腿上的浓密毛发足以成为一个问题,让我不敢露出多余的皮肤。
当我搬出家的时候,我为Sarah 2.0列了一个愿望清单。我雄心勃勃地放下了冲浪。
我想,最好先学会游泳。我是邻避的当地人无法封锁的西部,从中央车站乘坐40分钟的蜿蜒巴士到库吉海滩,坐在沙滩上盯着水看。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另一对衣裤也进行了长途迁徙。“我们要在这里呆上整整一天——我们花了足够长的时间才到这里,”他们边说边笑着打开行李,把每一分钟都当作美好的记忆储存起来,留着以后再用。
我的游泳之旅开始于我大学宿舍附近的一个城市游泳池里的几堂课,其中大部分是成年移民。教练说得很慢,鼓励我们抓着木板练习踢腿,疯狂地乱踢。我羡慕地看着白人在球队的车道上滑过,有时会把我推开,或者如果我不小心转向他们的车道,就会不耐烦地哼一声。
在这些时刻,我会感到尴尬,会为自己的迟钝而生气,会被轻松的游泳技巧所欺骗。我可以在每一次考试中都取得好成绩,在考试中也比英国人聪明,但游泳需要身体记忆,我想,在婴儿适应海洋和游泳池的假期中,这种身体记忆是无形地传递下来的。我不会游泳是我的穆斯林特征、我的非澳大利亚特征、我的多毛特征的一个隐喻:所有这些我已经习惯为之感到尴尬和羞耻的东西。
虽然这些最初的课程并没有让我走得太远,但我最终在20多岁的时候在奥本游泳中心(Auburn swimming Centre)的女性课后课程中学会了游泳。奥本游泳池位于悉尼西部,是移民游泳者的家。球队的泳道很轻松,休闲泳道和浅水池里挤满了孩子,他们的父母来自南亚、非洲和阿拉伯。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完成了在深水中游泳和漂浮的壮举。“我做到了,”我惊呼道,与带我去那里的那位戴着头巾的律师朋友击掌。参加活动的一些女孩戴着头巾,也有年纪较大的女性,她们全都脱下衣服,只穿比基尼、连体泳衣或紧身衣,这是一个习惯了怀疑和监视的社区。我不再谦虚,但我发现这些会议是心理上安全的空间。我不用担心种族问题,也不用担心那些跑得更快的游泳者会用肘部撞到我的脚。
我可以在每一次考试中都取得好成绩,在考试中也比英国人聪明,但游泳需要身体记忆,我想,在婴儿适应海洋和游泳池的假期中,这种身体记忆是无形地传递下来的。
在成长过程中,我对女性专属空间的狭隘感到恼火,渴望进入俱乐部和更广阔的世界,我认为那里才是真正的冒险和自由。回顾我的一些打破玻璃天花板的行为所付出的情感代价,我释放出这些聚会是多么珍贵,它们是抵御一个新的、并不总是欢迎的社会的毒箭和攻击的缓冲器。“安全空间”的概念经常被嘲笑,但在一个朋友们在公共场合被唾弃、被咆哮甚至被殴打的国家,问题不在于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些空间,而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空间。有一个舒适和自由的地方,你可以放松你的头发和充电。
“不过,还是要保持低调。我们不想再上演艾伦·琼斯的闹剧了,”一位游泳者在50米高的室外游泳池里漂浮着对我说。
几年前,也就是2002年,有人打电话给煽情的电台播音员艾伦·琼斯(Alan Jones),抱怨奥本(Auburn)游泳池有“穆斯林女性专用课程”。这名愤怒的呼叫者声称,游泳池被关闭了,这样穆斯林妇女就可以穿着“长袍”游泳。
琼斯尖刻地回答道:“什么?游泳池关闭了——这是一个公共游泳池——除了穆斯林妇女外,对所有人都关闭了?他们去那里,在他们所有的桶里潜水?”反应很快。随后,该中心收到投诉,当地一所女子学校预定的游泳课程被取消。
事实上,泳池已经被预订了,而不是关闭了。这难道不是这些右翼人士所称赞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吗?我的血液沸腾。他们拥有悉尼市所有的水资源,而在悉尼西部的这个小角落,这一小时,他们想从我们手中夺走。
围绕着水域的种族主义是澳大利亚文化的历史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针对土著游泳者的隔离一直在泳池中实施。在那之后,非白人并没有被官方拒之门外,但我们受到了更微妙的阻碍。
这就是新的种族主义产生的原因。这就像不受欢迎的孩子被蜂后边缘化,他们利用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来保持午餐室的最佳状态。水上经常是精英的空间——划船、游艇、海滩度假。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记者对他们对水的热爱有那么多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描述让我恼火的原因: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是澳大利亚人普遍的体验,实际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领域。
2016年,我实现了成为一名官方沙滩女孩的梦想。我喜欢征服我不应该去的地方,搬到Coogee的海滨郊区符合我所幻想的一种反向殖民主义:我闯入了一个世界,在那里邻避旅不需要我。我租了一套破旧的一室一室的公寓。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地区。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海滩上跑步、游泳和散步的人活跃起来,所有人都被水的精神召唤和热爱水的文化所吸引。
瓦拉纳西的祭司利用圣河来圣化信徒。在澳大利亚,海滩就是我们的世俗宗教。看着太阳从水面升起,落在地平线后面,感觉就像在精神上接近上帝,就像走进清真寺一样。我尊敬地脱下鞋子,赤裸着身子进入水中。我受膏受洗。
库吉位于联邦工党选区金斯福德·史密斯(Kingsford Smith),当时它有一条主街,不像邦迪那样自觉地赶时髦。在Coogee,你买不到印度茶或姜黄茶;这是令人安心的匕首。食物不太好;只有冰沙和碎鱼。其他棕色人种只有达美乐的送货员和赛百味的收银员。
但悉尼的文化和阶级差异的一个好处是,我可以消失在悉尼的这一边,没有人认识我。白人地区是年轻穆斯林约会的完美地方,远离窥探的目光。这种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是解脱的。我可以穿无袖连衣裙,让海洋的空气抚摸我的皮肤。
游泳救了我。我会在黎明醒来,像个梦游者一样去McIver的女士浴场。McIver是一个遗产名录上的海洋泳池,自1922年以来一直是女性专用的空间。隐藏在悬崖峭壁之下的泳池成为了外来者的天堂,光彩夺目地展示着裸露的乳房、赘肉、皱纹、毛茸茸的腿和“穿什么就穿什么”的气质。与邦迪的完美金发女郎不同,这个社会的外来者聚集在这里:穆斯林女性、年长的游泳运动员和酷儿群体。
我会在黎明时分醒来,把自己扔进冰冷的水里,和老McIver的游泳者们在一起。一旦浸入水中,我就觉得自己还活着。它抓住了我混乱的头脑,我盘旋的抑郁,我不稳定的心跳和不断的融入大海的想法。我神经上的冰冷就像一剂即时的药膏,看着太阳升起,我的身体在水中移动,我觉得我的心率减慢了。后来我在治疗中了解到,我不知不觉地被身体治疗和神经系统恢复治疗的冷水浸泡和锻炼所吸引。
当我在海洋中,沉浸在它的节奏中,我觉得我是在一种野性、自然和自由的怀抱中。生活就像波浪,很少是完美的,往往更加动荡。
节选自《德西女孩》,作者莎拉·马利克,8月30日出版。